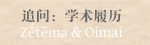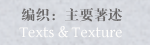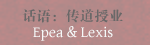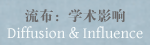| [米切尔 纳吉]《故事的歌手》再版序 |
| 作者 : 斯蒂芬·米切尔(Stephen A. Mitchell) 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 译者 : 尹虎彬 (YIN Hubin) 译 姜德顺(JIANG Desun)审译 | 点击数 : 49687 |
|
至迟到1930年代,无人能够搜集这种以极其自然的方式演唱的歌,那就是说,没有人为的打断。这种干扰,是由于一些录音技术性的局限所引起的。最终,帕里委托了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的音响专业公司为他准备了录音设备,该设备由配备肘节开关的两个转盘组成。设计周到的进退选择的转盘,使得正常情况下,在12英寸录音盘上只能录制几分钟的时间限制,得以无限扩大。在那样一个时代,大多数的田野工作者,无论是语言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还是民族音乐学家——使用各种各样的微型的录音设备如摄像机,帕里在他的一篇田野报告中说得很有眼光:“我已经写信给哈佛的商业代理,让他为我从铝制品公司再预订半吨圆盘,那大约是3000张盘。”(着重号由编者所加)。12 由于设计上的奇特,以现在的标准看来,这种设备的音质并不逼真,但很明显,它能使歌手持续地演唱,不会干扰他们作为创作者的设计,不受录音媒体的限定。突然之间,有了一种可以利用的东西,它很适合史诗的自然环境,这种环境,涉及到诸如以下几个重要的表演的层面:史诗的长度、停顿以及创作的特点。虽说帕里和洛德所使用的设备很落后,但他们极其小心地获取了高质量的材料。在他详细列出的支出说明里,帕里有这样的记录: “……我使用的音响设备,是由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的一个音响专业公司制作的,它的动力设计,是由一个6瓦汽车电池驱动的汽车发动机,从中可获得300瓦的阳极电压。设计者原来打算用电容器来抑制汽车发动机的静电,但结果很不成功,开始时汽车发动机的噪音传到扩音器和机械式录音磁头。幸而我一直注意调试电容器和发动机,灵活使用麦克风,在不受发动机影响的情况下进行录音。后来发动机干扰太大,已经挥之不去,如果我们想继续工作,在一个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录制,取得高质量的录音,我们就必须改进器械设计。我适时地将音响设备带到萨格勒布,向该地贝尔·爱迪生语音工作技师咨询。其结果是要用300瓦的电池来代替汽车发动机。这个新设备,我现在已经用了好些时间了。我觉得以前的录音圆盘不错,我现在制作的更好,它们的质量与铝制录音圆盘上的录音相比不差上下。”13 虽然帕里和洛德所使用的设备很笨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功能很差,听过本书所附录音光盘的人不会怀疑这一点。 接着1933年夏天的研究考察之后,帕里于1934年6月至1935年9月又回到前南斯拉夫做了更长一段时间的调查。这一次他有了以下九位助手,阿尔伯特·洛德、尼古拉·武伊诺维奇(来自赫塞格维纳斯托拉克的歌手)、伊布罗·贝卡(也是来自赫塞格维纳的歌手)、哈姆迪亚·沙克维奇、伊布拉欣·赫鲁斯塔诺维奇(“两个穆斯林”,他们搜集到许多妇女歌)、伊利亚·库图佐夫(在杜布罗尼克任体操教练的一位俄罗斯移民,1934年移居贝尔格莱德),还有几位打字员。14 在为期15个月的搜集活动中,帕里及其助手们汇集了12,500个文本,大都为抄本,还有大量的录音资料,大约有3500个12英寸铝制音盘。 英雄歌(junacke pjesme),妇女歌(zenske pjesme), 与歌手的对话,他们录制的乐器演奏段子,这些东西本身就很令人吃惊。他们的巨大工作,有时候不免要遮蔽他们所完成的更重要的一些成就。帕里的意图,并不仅仅是观察和记录口头传统,与此相一致,他和他的同事们对他们搜集到的资料表现出极大热情,并对材料的实验研究方法也表示出极大热情。的确,帕里的田野笔记和报告表明,他对自己所搜集的材料很满意。但是,从1937年帕里的助手阿尔伯特·洛德的手稿中,从他作为一名普通听众的角度,我们方才得到了一种活生生的印象,了解到了事情的原委。(这里所列出的人物数量与附有图片的文章是一致的,这些图片可在CD中找到): “寻找歌手的最好办法,是到土耳其的咖啡馆,在那里交些朋友。这是集市日子里农民活动中心,也是斋月期间夜生活的娱乐场所。我们在小街上发现了这样的场所,走了进去,要了杯咖啡。离我们不远的长凳上,坐着一位土耳其人,用一个银制的雪茄烟嘴吸烟。他人很瘦消,高个子,很有吸引力。(图27)在我们谈话间歇的当口,他加了进来。他认识歌手。他说,最好的歌手当然是一个叫阿夫多·梅迪耶维奇的人,一个农民,家里离这儿有个把小时的路程。他有多大了?60,65岁。他会念书写字吗?不,老兄!(Ne zna,brate!)于是,我们去找他,给我们的新朋友贝根(Began Ljuca Niksic)要了一杯咖啡。贝根不是一般的人。在尼克希奇远近闻名的默罕穆德将军之子,穆罕默德曾领导土耳其人守卫尼克希奇,贝根曾被尼古拉国王召进宫中担当副官(图28)。在我们等待阿夫多到来之时,贝根讲述了他的经历。 阿夫多终于来了(图29)。他给我们唱了老萨利赫最喜欢的段子,苏丹·萨利母时代攻打博格达的故事。我们听着,对这位身材矮小的朴实的农民越来越感兴趣,他的喉咙因为巨大的甲状腺肿而变形。他两腿交叉地坐在凳子上,拉起古斯莱(gusle),伴着乐曲的旋律摇动身体。他唱得很快,有时顾不得音调,随着琴弓在弦上来回轻轻的滑动,阿夫多以最快的速度口述诗行。聚拢了一大群人。镇子里一群现代小青年,玩着扑克牌,他们一直吵闹不停,后来也散伙了。 接下来的几天有了新的发现。阿夫多的歌,比我们以前接触到的任何一部歌,都要长、都要好。他可以把一部歌拉长,一直演唱几天。有些长达15000行到16000行。别的歌手也来了,但无人可与阿夫多相提并论,他是我们南斯拉夫的荷马。”15 “我们南斯拉夫的歌手”告诉我们,这句话含纳了帕里-洛德“理论”,该理论引起了古典学者们之间的一个方兴未艾的争论,争论到底如何界定“他们”的荷马。《故事歌手》的民族志也反映了古典的渊源:洛德的前言是这样开始的:“这是一部关于荷马的书。他是我们的故事歌手。”在洛德第一段的最后,阿夫多成了南斯拉夫的荷马:“他是我们今天巴尔干的故事歌手”。阿夫多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的身上放射着荷马的光辉。古典主义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16 帕里和洛德在自己的民族志研究中,尽量避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问题。虽然如此,“我们的南斯拉夫的荷马”,与巴尔干正在进行的政治分歧和意识形态的斗争相关联。为了理解这种关联,我们可以从一个政治的套话出发,这是由一位巴尔干学者,在涉及南部斯拉夫口头传统时谈到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用同一种语言吟诵,遵循同样的格律限制,他们使用相同的程式化的主题材料。他们之间的区别,则是英雄或反面人物的民族自我意识,以及歌的长度。”17 这里需要补充的重要一点是,前南斯拉夫政府到了1971年,才对穆斯林赐予了官方的名称。18 就基督教的口头诗歌而言,一位有名的人物是塞尔维亚的民族志学者和文化领袖 卡拉季奇(Vuk Stefanovic Karadzic,1787-1864) ,他出版了一部典律性四卷本集子《塞尔维亚民间诗歌》(Srpske narodne pjesme),它反映了所谓的科索沃歌的全貌。关于它的意义传统上是这样表述的 : “塞尔维亚基督教歌,被塞族人视为塞尔维亚民族意识的唯一表现。而科索沃歌更是如此。这些歌讲述了1389年科索沃战争相关的事件、情感,此次战争塞族败于土耳其人。根据歌的文本,塞尔维亚王子有两个选择:在人间获胜,或者,在人间战败而在天堂获胜。因此,塞尔维亚人的战败,在歌中显得很光彩,在塞尔维亚人的心中,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胜利。”19 另一位出版塞尔维亚口头传说的著名人物,是佩塔尔·佩特罗维奇·涅戈什(Petar Petrovic Njegos,1813-1851)。他和武克一样,对塞尔维亚基督教的民族意识的形成起关键的作用。20 在《故事歌手》里,洛德对穆斯林传统的口头诗歌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在沙拉热窝也是这样,穆斯林经常根据《克罗地亚中心出版社资料集》,或者根据赫尔曼(kosta Hormann)的集子进行大量的再创作。这些活动大都起源于本世纪初,特别是1918年以降。”21 洛德指出,穆斯林口头传统与基督教传统相比,较少受到经典出版物文本的影响。洛德的观点表明,帕里集中搜集穆斯林的歌,其原因正在于此。和帕里一样,洛德对于穆斯林和基督徒在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并末给予价值判断。22 相反,他追随帕里,发展科学的研究方法,探索书面印刷语言对口头传统的影响。对于帕里和洛德来说,实证的材料证明,印刷品的意识形态,对于他们所分析的各种南斯拉夫文化的口头传统的稳定性是有影响的。当洛德把这种不稳定性称之为侵染口头传统的“疾病”时,他指的是印刷品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书面词语本身:“尤其在基督教人口中,青年人几乎都受到这种疾病的感染。但对穆斯林来说则不完全这样,因为他们的集子,并无哪一部被赋予了武克或涅戈什式的近乎神圣的权威。”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即共产党的南斯拉夫时代,洛德作了如下评价:“学校教科书上的一般精神食粮,一直来自武克集子里的歌,最低程度也是来自涅戈什的作品。学校教师在歌的搜集过程中起很大作用,这些歌的印刷形式大都出自他们以及那些年轻人之手。”23 Continuing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文章来源 : 译者提供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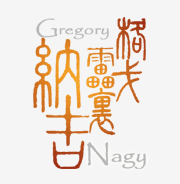
· 国际史诗研究者档案 ·
Archive for International Epic Researchers